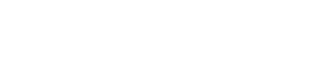從“北洋機器局”到“德州兵工廠”
原標題:從北洋機器局到德州兵工廠
從北洋機器局到德州兵工廠
井振武唐景元周醉天
作者按:這是一份有關東局子究竟去哪了的調查報告。作者井振武、周醉天于2019年8月赴德州實地考察。在德州文史朋友張明福、唐景元等人的陪同下走訪了運河畔的德州兵工廠舊址,并同德州文史朋友大家座談。唐景元是當地的一位著名企業家,早年曾在德州兵工廠舊址小學讀書,熟悉當地的歷史掌故,與德州兵工廠在各地的后人聯系密切。
有關這一問題研究因史料奇缺,一直很少。自天津學者李程遠、徐蘇斌與華中學者陳國棟在英國圖書館發現1904年英國湯姆森上校參觀德州北洋機器局繪制的機械局平面圖后,引起學術界關注,有關研究熱絡起來。2020年7月18日,《今晚報》天津衛版發表吉鵬輝《北洋機器制造總局照片真相》一文,指認德州北洋機器制造總局大門的照片,引起津門學者興趣,在德州文史圈引起熱議。8月1日,天津衛版有刊登了張明福《存世22年的德縣兵工廠》一文,遙相呼應,印證歷史。一段封存已久歷史往事重新回到人們。故而特授權《天津記憶》發表這份調查報告,以加深大家對過往歷史的了解。
一.天津北洋機器局的由來
天津是近代中國洋務發軔較早的地區之一,也洋務運動在北方的重要支點。有鑒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僧格林沁鐵騎敗走海門洞開,英法聯軍長驅直入,不但占領天津,還攻陷京城,圓明園遭焚,社稷難保的教訓深刻,1866年9月初,總理衙門王大臣、恭親王奕訢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分別向清朝皇帝提出建議,設立天津機械局,制造軍火,編練洋槍隊。他們的主要理由:一是練兵之要,制器為先,直隸既欲練兵,自當就近添設總局;二是仿效外洋生產各種軍火,以備南局(江南制造總局)生產不足所需,一旦有事,取運甚易。⑴由于天津臨近海口,購料取材、雇傭洋師、制造方便,具有拱衛京畿,以固根本的重要意義,很快獲得朝廷批準。
崇厚遂聘請英國人密妥士代為采購機器,覓雇工匠,撥銀八萬兩,購買制造火藥、銅帽等機器設備;通過北京英國馬隊總教官薄郎認識了一位英國人,從香港、上海購買機器;由江南制造局代購大型設備。推薦奉天府尹德春來津差委,總理機器軍火總局、高從望仁擔任提調、黃惠廉任翻譯。從同文館選調數人,一部分辦理文案、采辦轉運等文差;另一部分從事制造,悉心講求,得西法奧妙。招聘的外國技師春間先后到局,由密妥士分派各司其事。還請英國人狄勒先行試辦。并派京營25歲以下員弁跟隨洋人學習技藝。相關費用將津海關、東海關洋稅扣出四成銀兩,隨時提撥應用,以濟急需。
1868年,勘定在于天津城東十八里賈家沽地方,設立火藥局,是為東局,占地計22頃30余畝,初名天津軍火機器局(上圖)。春間,外國技師送來了建筑廠房、宿舍的圖紙,正式開始興工建設,局內共建機器等房42座,計290余間。大煙囪十座,洋匠住房160余間。⑵至1970年8月告成,前后耗時3年多,用銀388000兩。
1870年9月,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接辦天津軍火工業,更名為:總理天津機器局,通稱天津機器局。他親往局址查勘,看到垣屋尚須加修,機器尚需添制,火藥亦尚未開造,于是詢問密妥士火藥制作情況,逐事核實。并認為:雇傭洋匠,進退在我,制器這種要害部門長期被外籍人把持,存在尾大不掉的危機。非廉正熟悉而有調理之員,不足以謀。于是,罷黜不懂機器的洋總管密妥士;推薦、任用沈寶靖出任總辦,以主其事。啟用在津養病的陳欽并授津海關道銜,擔任會辦操持局內事務,還命幕僚劉含芳為委員參與其中,從南方調來大批熟悉生產制造軍火的技術工人,又淘汰、解雇毫無經驗的旗人與漢人。
從1873年至1892年李鴻章對天津機器局進行了五次較大的擴充:一是1873年春,新購的四架洋藥碾到齊,添購各式機器十余臺,建成第二座碾藥廠和新建機器房,將原設在西局的鑄鐵廠遷往東局。并在北郊浦口購地59畝,建成洋式藥庫三座。同時,第三、四座碾藥廠建成開碾,淋硝、磨磺、燒炭等部門各在原廠房增添器具,提高產量,以供四個碾藥廠的需要。二是1875年修造了一座制餅藥的新廠,裝置新購六角藕餅藥機器,專門制造后堂鋼炮所用餅藥。并將機器房一半分出來,為洋槍廠。添購了制造林明敦槍及中針槍子的機器,添設卷槍爐房,把原銅帽房一半分出,為槍子房制造槍彈。此外,還添設硫酸廠、軋銅廠和配造拉火的新廠。經過充實提高,天津機器局較具規模,開始生產。三是擴地4頃,1876年春開始至1882年,添設了電氣水雷局。又添設了提磺廠,壓藥房,設分藥、切藥等房、添設淋硝廠、增建硫酸廠,有鉛房六間。并在韓家墅建新藥庫一座。四是1887年,興建了一座制造栗色火藥工廠。聘請外國技師約士設計,由總工程師司徒諾負責安裝,成為世界最大最好的火藥廠。還在機器局旁創建了北洋水師學堂。五是設立寶津局(又名北洋制幣廠,下圖)。1892年,又建設了一座煉鋼廠,從英國購進成套煉鋼設備,以及鑄鋼爐、軋鋼機、起重機等大型機械、用具等。第二年正式投入生產,這是中國北方第一座近代化規模較大的煉鋼廠。⑶另外,還修建了老龍頭車站至機器局的鐵路專用線。由于天津機器局占地26頃89畝,地域廣大,廠與廠之間距離較遠,因此設置了連接各個廠、庫房的手動有軌鐵輪車。
天津機器局經過李鴻章大規模地擴充建設,逐步成為一個機械制造、化學化工、金屬冶煉、鑄造、熱加工、船舶修造等,具有多種生產能力的大型軍火企業。常年雇傭工人達2700多名,生產品種逐漸增多,計有:火藥、銅帽、槍子、炮彈、拉火、水雷、洋槍、洋炮和其它軍用物資,其中以火藥、銅帽、槍彈、炮彈為主要產品,至1880年年生產量為:各項洋火藥為六十余萬五千三百五十磅;銅帽二千五百二十七萬粒;林明敦后門槍子一百十八萬七千顆;毛瑟后門槍子二十七萬三千四百顆。炮彈兩種:前膛開花炮彈六萬余顆,后堂來福鍍鋁大炮彈五、六千顆,最高達九千顆。其生產的軍火除主要供給津京地區駐軍外,還供應河南、熱河、察哈爾、黑龍江等北方各省軍需。另外,還生產挖泥船、小火輪、布雷船、水底機船,以及行軍橋船等等,被李鴻章稱為洋軍火總匯。
1895年,王文韶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下圖),將天津機器局改稱為總理北洋機器制造總局,北洋機器局由此得名。
二.庚子之役遭受滅頂之災
1900年6月16日深夜,八國聯軍攻打大沽口炮臺,悍然發動侵華戰爭。清兵被迫自衛反擊,聯軍不斷增兵,激烈的戰爭在天津周邊打響。俄軍步兵團2000余人開到天津老龍頭車站,在面對英租界方向的海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橋,占領天津老龍頭車站與北洋機器局之間的開闊地帶,還設立營盤駐扎。這時,有200名德軍攻打北洋機器局,被守軍打死12人,打傷25人,鎩羽而歸。據一名叫馬克里希的聯軍人士記述:北洋機器局這座大面積的建筑群位于英租界以東二三英里的地方,是華北最重要的軍火工廠。工廠中雇用了將近2000名工人,制造地雷、炮彈、棕色棱柱火藥、無煙火藥、普通黑色火藥、硝棉火藥、毛瑟槍子彈等等。工廠中的機器總價值估計遠在100萬英鎊以上。工廠占地大約在4/7到5/7平方英里。⑷這里常年守備有兩個營盤的清兵,共計1000人。在機器局周圍,以及通向南面的道路上埋設了自己生產的地雷,阻止聯軍進攻。27日(星期二),在俄軍斯捷謝利將軍指揮下,從透力勃爾號軍艦借用了12磅大炮,及小口徑野戰炮,上午九點開始攻擊,采用地毯式炮轟掃清道路上的地雷,并延伸向北洋機器局內傾瀉。幾分鐘后,許多大車間著起了大火。在英國海軍陸戰隊、德軍、美軍和日軍約800人,以及剛從威海趕來的華勇團第一營的支援下,俄軍利用壕溝潛伏、接近圍墻發起沖鋒,守軍在營官潘金山率領下頑強抵抗。戰至中午,潘金山負傷,這時一顆炮彈落在大火藥庫引起巨大爆炸,地動山搖、震耳欲聾、煙柱騰空、火光沖天,彌漫的濃煙遮住視線。大約千余名大清援軍前來助戰,從外圍接應北洋機械局的守軍,戰斗十分慘烈、膠著。經過4個小時激戰,在下午1點30分俄軍才攻陷并占領了天津東北的北洋機器局。⑸是役清軍傷亡營哨弁勇三百余人。⑹擊斃俄軍七人、擊傷五十一人;擊斃英軍四人,擊傷十五人。其他聯軍擊傷九人。俄軍將北洋機器局視為獨有的戰利品,并升起俄國旗。在局內瘋狂破壞,其中珍貴的各種科學儀器及航海設備均被占領者銷毀殆盡。
7月14日,天津城陷落。30日,八國聯軍在直隸總督行館成立天津城臨時政府委員會,對天津實行殖民統治。與此同時,頒布了《天津城行政條例》。在第四、第五條規定委員會有權根據需要支配除軍事部門以外的政府所屬財產和不動產,并且有權出售被沒收的當地華人財產,包括不動產和動產;有權支配撥給委員會作為必要費用開支的款項。⑺根據這項規定清政府在津的所屬財產和不動產均成為臨時政府聯軍的戰利品,任由臨時政府支配,可以售賣或拆除轉化為日常開支經費。
臨時政府以安全、衛生為由,制訂了拆除天津城墻計劃,通過承包商,實施拆除。并把北洋機器局視為一塊流油的肥肉,8月8日通知秘書長起草一份致俄軍司令部的函,由本委員會簽發,建議提取目前被俄國軍隊占領的東機器局內的銅錢。⑻接著,由公共工程局局長起草了一份關于東機器局內的機器清單,表示委員會有可能需要這批機器。⑼這時,臨時政府與俄軍當局在新浮橋歸屬問題上發生摩擦。新浮橋位于現在的金鋼橋位置,由俄軍控制并在橋上懸掛著俄國旗。俄軍官要求臨時政府同意新浮橋歸屬權屬于俄軍。由于臨時政府沒有同意,于是控制浮橋的俄軍就刁難臨時政府派去管理橋的人員,干涉他們開啟和關閉浮橋。⑽第二年1月18日,當臨時政府要求行使對北洋機器局機器資產處理權時,俄軍當局表示說把東機器局內的機器送給臨時政府,具體日期待定,⑾碰了軟釘子。23日,俄國部隊參謀長致函臨時政府說,可以為委員會提供所要求的東機器局的物資,但為了得到這批物資,有必要與俄國‘博比埃號’艦艇司令官磋商。⑿由于臨時政府就是一個草臺班子,其委員由各占領軍提供人員拼湊,行政執行力有限;再加上北洋機器局地處城北區與軍糧城區的交匯地帶、遠離城廂,長鞭莫及;以及賴以運輸的運河水位極度下降,加上戰爭摧毀道路,通往火車站、法國橋的道路上彈坑累累、坑洼難行,臨時政府拿不走機器,俄國當局也不便處置,就這樣北洋機器局的事被拖延下來。但偷盜機器零部件的事連續不斷發生。
臨時政府在不遺余力地拆除天津城墻的同時,又得不到東機器局機器設備變賣的情況下,對海光寺淮軍行營制造局(又稱,西機器局)進行了瘋狂兜售。與一位叫湯姆遜的商人簽訂了合同,公共工程局呈交了一份海光寺機器局的機器和鐵制零件的清單,總重量為11626.06英擔(9369.31擔),這一數量和委員會與湯姆遜先生所簽訂的合同數量完全相等,由此臨時政府獲得全部費用,總計2137.42元。⒀接著,在日軍當局要求下,公共工程局下令湯姆森在兩周內將全部機器和廢鐵統統提走,就這樣淮軍行營制造局在天津徹底消失。與此同時,德國法根海少校出面將西沽武庫徹底炸毀。德國德義洋行及一些商人私下倒賣西局、以及武庫的物資與彈藥,大發國難財。
1901年1月15日,清廷議和代表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遵旨在《議和大綱》上簽字畫押。并與11國代表繼續進行議和談判。在談判期間,八國聯軍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以出兵山東、山西相威脅。當清廷議和代表應允如數賠款后,聯軍總司令、德國陸軍統帥瓦德西下野,6月3日離開北京回國。這期間,八國聯軍及天津臨時政府解除中國人民反抗能力的暴行一刻都沒有停止。7月22日,法國在華部隊司令官華倫,根據聯軍司令官會議決定通知天津臨時政府,拆除臨時政府管轄區內下列防御設施:(1)天津的西沽武庫、黃炮臺、黑炮臺及東機器局。(2)軍糧城的2座兵營。(3)新河的3座兵營。(4)大沽所有防御工事;(5)北塘所有防御工事。24日,臨時政府討論拆除炮臺問題,并發信寄發給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及俄國指揮官。⒁9月6日,臨時政府批準公共工程局對拆除工作采用訂立合同或其它方式,要求既要價格低廉,又要保證工程迅速完成。第二天,《辛丑條約》在北京簽訂。
有了尚方寶劍,臨時政府重新啟動對北洋機器局的設備處置事宜,將機器局附近的某些建筑約20萬塊磚,賣給自來水公司;把機器局儲存的火藥出售給開平礦務局;銷毀了存放在局內的700支斯普林費爾德步槍;將鑄幣局化掉的純銀及銀元寶,賣給了摩爾根的代理人木勒;一些洋行、商人乘機將東機器局的鉛砂購走、倒賣并拆除機器;部分物資及硫磺、硝石等,由道臺張蓮芳、海關道唐紹儀、鹽運使楊宗濂等人通過各種渠道,安排外運。然而,臨時政府與商人談判簽署拆除北洋機器局合同一事并不順利,這為機器的存續提供了時間。先前的合同還沒執行,即被推翻。直至1902年4月28日,才與一名叫奧利弗羅那的商人簽訂用費13200元的拆除合同。截至5月底,臨時政府為拆除北洋機器局支出費用計7000元。由于臨時政府面臨解散危機,一些官員紛紛為自己挖門子找后路,官場上也出現了一些通融情況。一直堅稱不予售賣的北洋機器局軋幣設備,在署理直隸總督袁世凱提出要求后,遂將軋幣設備無償地轉讓給了袁世凱。⒂于是,派周學熙任總辦北洋銀元局,選擇在河北窯洼大悲院護衛宮址建廠,招募工匠于當年12月建成投產。在風雨飄搖的檔口,多方勢力博弈,僅用3個多月時間,處理掉一座龐大工廠群,既要拆除廠房、又要售賣機器,是無法實現的。袁世凱在天津政局中顯露頭角,為臨時政府清單上的北洋機器局機器設備的保留與購買提供了可能。至于哪部分從商人手中購得;哪部分從臨時政府手中接收,可能永遠成為了謎團。隨著時間的推移,北洋機器局在天津徹底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在北洋機械局設備處置上有沒有利益交換,今天我們無重知曉,但知道是:天津臨時政府秘書長田夏禮、以及漢文秘書處部門首長丁家立,都被袁世凱啟用,前者被袁總督聘為顧問;后者被袁總督聘為掌管直隸教育的要員。
三.搬遷德州復建北洋機器局
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去世。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上圖),負責辦理恢復對天津的管轄。袁派津海關道唐紹儀等人入住天津租界內接洽理事,并指派有關人員收購臨時政府及商人們倒賣的東、西兩局部分機器設備,為日后恢復作打算。第二年2月,袁世凱奏請武衛右軍軍務處精選正定、大名、廣平、趙州、灤州、冀州等縣壯丁6000人,分領訓練,至5月北洋創練常備軍,再添練兩鎮四協共19120人,駐扎保定東關,號稱新練軍。⒃軍隊擴大使得彈藥需求量猛增,恢復軍火企業勢在必行。但根據《辛丑條約》規定,在天津二十里之內不許中國駐軍,一切有關軍事設施均遭摧毀,連袁世凱親兵衛隊都只能駐扎在韓家墅,⒄因此在津復建北洋機器局已無任何可能。4月3日,天津臨時政府召開專門會議,提出天津地區臨時政府委員會關于該政府移交中國當局的建議書,表示移交當天,總督的出席是非常有益的,⒅表明臨時政府解散進入倒計時,希望政權移交有賴于得到袁世凱的支持。此時,臨時政府忙于善后,外國軍隊相繼開始撤離,官員自找后路,管理松弛、市面上盜竊橫行,陷入一片混亂。袁世凱向德州運送物資,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比如:6月4日,漢文秘書要求為總督從天津運軍鞋和衣物前往德州兵工廠發放通行證。總督的要求是通過其驛站官員雍某提出的,已令司庫簽發。⒆可見,袁世凱遷徙北洋機器局的工作已經鋪開。7月中,清廷議和代表、兵部尚書銜周馥奉命與各國使臣就交還天津事在京敲定。月底,臨時政府停止漢文秘書將會議記錄譯成中文工作,把以前譯的中文底稿全部銷毀,殖民統治處于停擺。⒇8月15日,袁世凱接管天津主權,由都司曹嘉祥領導的警察部隊控制局勢,臨時政府即刻解散。拆除中的北洋機器局一并收回,殘存部分機器亦在歸還中。
隨后,清政府實授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新練軍隊不斷擴大、京畿及直隸、山東、遼寧等地防衛亟待加強,軍火企業復建迫在眉睫,于是選定德州。袁世凱早在1899年12月率部途經德州時,即接到署理山東巡撫諭旨,故視德州為自己福地,熟悉當地情況。
德州,古稱安德,簡稱德,位于山東省西北部、黃河下游沖積平原,是山東省的西北大門。今德州市地理位置位于黃河下游北側,東經115°45′—117°36′、北緯36°24′25″—38°0′32″之間。北以漳衛新河為界,與河北省滄州市為鄰;西以衛運河為界,與河北省衡水市毗連;西南與聊城市接壤;南隔黃河與濟南市相望;東臨濱州市。距北京320公里,距天津227公里。德州市基本氣候特點是季風影響顯著,四季分明、冷熱干濕界限明顯,春季干旱多風回暖快,夏季炎熱多雨,秋季涼爽多晴天,冬季寒冷少雪多干燥,具有顯著的大陸性氣候特征。光照資源豐富。德州市平均無霜期長達208天,年平均降水量為547.5毫米。德州自古就有九達天衢、神京門戶之稱,是全國重要的交通樞紐。歷史上德州大部分時間隸屬于山東,亦有隸屬直隸之時,處在直隸山東交界處,戰略地位十分突出。又是京杭大運河的一個重要碼頭,是南北文交流、交通之要地,是南方九省(冀、魯、豫、蘇、皖、浙、湘、鄂、贛)通往天津、北京的重要漕運通道,京杭大運河穿越轄區140余公里,交通便利,遂決定把德州作為復興軍火企業之重地。
1902年初夏,署理直隸總督袁世凱一方面派人到當地選址購地,規劃設計,建設廠房;另一方面將買回東西局殘毀機器,即在天津租界內賃地存儲,招募工匠、擇要修理,(21)并陸續運往德州,運送工作一直持續到第二年6月。還從英、德等國進口了部分機器設備。據《天津機器局大事記》記載:閏五月初六(6月30日),東局子殘毀機器等件裝船三十余只運往德州。《大公報》也報道說,所剩余器具再裝船十只,即可運完。(22)復建的北洋機器製造局選址在德州西門外運河碼頭東岸的花園,占地700畝,它西枕京杭大運河,南至豆腐巷、北至上碼頭村(今黑馬蔬菜批發市場北界),其間碼頭林立。復建后仍稱北洋機械制造局,第一任總辦,就是1899年在天津北洋機械局擔任總辦的王仁寶。(23)
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是王仁寶具體主持了機器、人員遷移和北洋機器局在德州的復建。從德州博物館收藏的歷史圖片顯示(上圖),人們推車肩扛運送機器設備,遷移隊伍浩浩蕩蕩,前后望不到頭。天津北洋機器局前后存世30余載,培養了一大批熟練技術工人和專業技術人才,他們為北洋機器局復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術支撐,工業文明以這種方式擴散到德州,給古老運河碼頭、商業小縣城~德州帶來了近代工業文明的火種,成為該地區近代化的起始點。
四、德州北洋機械制造局概述
德州北洋機器制造局(以下簡稱德局)從1902年初夏開建,至1904年8月底建成,10月投產。
(一)經費:北洋機械制造局自1904年建成投產,從1905年開始,其運營經費,來自三個海關的稅收中提取,直接解交德州北洋機械制造局。計江海關(上海)按稅收總數的六成提取,東海關(煙臺)每年按四成提取,津海關(天津)按四層提取。(見下表,單位:庫平銀。1902-1904年資料缺失)
光緒28年-30年八月(1902-1904)
光緒30年九月-31年十二月(1905年)
光緒32年
(1906年)
光緒33年
(1907年)
上年結余
333549
109598
152926
當年新收
660232
643753
806779
江海關解入
199672
100000
100000
東海關解入
150000
100000
108612
津海關解入
307800
441009
595532
薪資扣存平余
2760
2744
2635
當年總計
993781
753351
959705
自1908年(光緒34年)開始,北洋機械制造局的經費改由海防支應局按各項用途定額發給銀兩。其中制造經費定額每年44萬輛,遇閏月加銀36667兩,額定造子彈一千萬粒,如添置機械、續建工程或者其他一切等項,須另案請款。防護隊薪工口糧從前由常年經費項下開支,也改為另案請款。官醫處薪水藥費每年定額2400兩,遇閏月加銀61兩。1908-1910年經費情況詳見下表:
光緒三十二年(1908年)
宣統元年
(1909年)
宣統元年
(1910年)
上年結余
229786
29000
5968
當年新收
659567
621301
506912
制造經費
440000
476667
380000
防護隊薪工口糧
8298
10808
13371
武庫薪水公費
1090
官醫處薪水藥費
9280
2461
補發購買機械物料
補發添建工程等款
9422
25888
111880
39813
劃還訂制槍子、器件工料價款
81359
18395
73728
本局扣用平余
85320
當年總計
889353
650301
512880
清末時期,北洋機械制造局每年須造表、呈遞《收支銀兩大數四柱報銷總單》,將本年度經費分為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就是四部分,分別呈送給陸軍部和度支部核銷。
民國以后,北洋的行政職權不在,德州北洋機械制造局改隸陸軍部軍械司,遂改名德州兵工廠,1913年改名德縣兵工廠,全部經費也由陸軍部軍械司定額發給,初期每月撥款京平銀3萬兩,后因擴充營房等項目,追加3千兩,每年合計撥款京平銀39萬6千兩,合庫平銀37萬兩,后改為銀元,每月發給455833元,每年合計55萬元,數量較清末減少一半兒,并不能保證按時發放。(24)
(二)管理人員:
清末時期德州北洋機器制造局長官稱總辦(總理局務,副將銜),以下有會辦、提調、監理分別幫辦局務,總管廠務,制造軍火。
下設文案處、收支處、報銷處、稽查處、工程處、官醫處、物料庫、軍械庫、還有駐津收支處和轉運所。各處、庫、所,都設有正委員、副委員、司事、書識。
民國時期德縣兵工廠長官先稱督理,后稱總辦,將軍銜,以下設會辦。
下設機構有庶務股、書記股、會計股、統計股、采辦股、工務處、審檢處、材料處、軍械庫、稽查所和軍醫所,各處設處長、處員、司事、司書;個股設股長、股員、司事、司書。
主要負責人列表如下(表中空格及文字,有疑似錯誤之處均系原狀):
總辦
簡歷
任職時間
會辦
簡歷
任職時間
王仁寶
曾任按察使(臬臺)
至光緒三十二年
鄭嘉榮
直隸候補道
劉冠雄
副將銜補用游擊
三十二年至
李祥光
副將銜補用游擊
光緒至民國三年四月
言敦源
至民國元年四月
魏允恭
民國元年四月至十一月
王亨鑒
中將銜,陸軍部少將
民國元年十一月至民國四年
譚鼎和
兼工務處長候補縣丞
民國三年四月至九年九月
謝幫清
民國四年至六年四月
宋振綱
民國六年四月至九年八月
陳源亭
北洋水師輪機學堂畢業
民國九年八月至民國十二年六月
簡業敬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陸軍少將
民國九年十月至年十一月
高振魁
陸軍中將
民十二年六月至十三年十一月
武文炳
無煙藥學生,陸軍炮兵中校
至十三年十一月
費國祥
陸軍少校
民十三年十二月至十四年七月
張化南
陸軍少將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至十四年月
張宣
民國十四年七月至十一月
吳柏琴
民國十四年月至十一月
(25)
(三)規模:
自1902年初夏開始動工,除將天津修理好的機器全部運來外,又從英、德等國進口了部分機器設備。經兩年的施工,于1904年8月底完工,10月投產。
德州北洋機器制造局復建共有十三個分廠。分別是:機器廠、桿彈筒子廠、快槍子廠、新槍子廠、無煙藥廠、棉花藥廠、鏹水廠、木工廠、磷硝廠、木樣廠、鑄鐵廠、熟鐵廠、造帶廠、鍋爐廠等等。機器局內設10個機構:即文案處、收支處、報銷處、稽查處、工程處、官醫處、物料庫、軍械庫,還有駐天津收支處和轉運所。大量機器設備的搶救以及轉運,使德局得以復建,為中國北方保留下一股工業基礎的血脈,具有積極意義。(26)
上世紀正在建設中的德州電廠機房 王德勝提供
當我們與天津北洋機器局(以下簡稱津局)對比分析后發現:一是德局占地面積僅是津局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規模較小。二是印證了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期間,津局的碾藥廠、洋式藥庫、軋銅廠、拉火廠、水師學堂,以及擁有尖端技術的餅藥新廠、電氣水雷局、煉鋼廠等等,均遭到毀滅性摧殘。使得復建后的德局在研發制造能力上受到嚴重制約,德州博物館展示的一份《1906-1909年德州北洋機器局產量圖表》表明,德局已經沒有能力生產槍支、大炮、水雷、地雷、炮彈和火輪船了。
德局1907年陸續擴建,新建廠房113間、辦公樓一座、在廠外東南方建了彈藥庫、紙盒廠(造紙廠)、造酒坊等設施,廠房計達635間,辦公房和庫房達485間。后來在其東邊又修筑了津浦路,交通運輸更加便利。
德州北洋機器制造局發電車間 王德勝提供
老電廠機房文保牌 王德勝提供
老電廠機房內景 王德勝提供
德州發電廠,在兵工廠舊址一側修建 筆者拍攝
1909年從天津購買了兩臺鍋爐和兩臺發電機,全廠安裝了電燈,這是德州第一批電燈。雇用工人也擴大到3000人,在津局師傅們的培養下,德州第一代產業工人誕生。1949年6月25日,德州市第一屆職工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全市職工有6474人。
德州兵工廠的固定資產,有房地產和機械設備,首先是買地,前后一共買了民田850畝,每畝價銀按5兩計算,大約計有4000多兩,然后建造廠房、庫房、辦公房,大約1120間房屋,工料款計約35萬兩上下。
機器設備,德州兵工廠各分廠的機器設備,先期是原天津北洋機械制造局,被八國聯軍焚毀的,經過了修理還能使用的;更多是后期陸續由英國和德國購進的。根據民國五年1月,德縣兵工廠《購存各種物料數目價值產用途月報表》所附的機械類統計:
十幾個分廠,一共有各種機器設備760余部(臺、套),價值452025兩銀子,以上三項合計,德州工廠固定資產合計庫平銀806000兩銀子。(27)
碑文:中華民國元年秋季北洋制造局造。唐景元提供(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兵工廠舊址的職工宿舍發現的那塊殘碑)
(四)產品:
北洋機械制造局自1904年9月開始投產,最初兩年主要制造7.9毫米槍子,年產僅600萬粒,以及少量7.5厘米日本炮彈底火和克虜伯7.5厘米炮彈底火。到1907年增加了6.5毫米槍子,后來制造的軍火品種逐漸增多,計有:
槍子類:七九帶箭槍子、七九無箭槍子、七九尖箭槍子、六五帶箭槍子、六五無箭槍子、丹麥式機關槍子、曼利夏槍子、村田式槍子、自來德手槍子、布朗林手槍子、和六五假箭槍子。
炮彈底火類:格魯森5.7厘米炮彈底火、日本7.5厘米炮彈底火、克虜伯7.5厘米炮彈底火。
炮彈碰火類:格魯森炮彈碰火、37毫米炮彈碰火和6厘米炮彈碰火。
炮彈類:6厘米開花炮彈和37厘米開花炮彈。
藥水類:硝鏹水、黃鏹水、黃噫噠(供本廠泡藥棉、洗銅盂、造白藥、制無煙藥用)
火藥類:棉藥坯和無煙藥。
槍彈配件類:各種槍子銅殼、槍子底火、槍子箭頭、銅子夾和鋼子夾。
銅皮類:底火銅皮、子夾銅皮、紫銅皮、和炮子銅皮。
軍用器械類:鐵子彈箱、大小鐵锨、大小洋鎬、大小洋斧。
從兵工廠的軍火生產數量看,每年實際制造各種槍子1500萬粒至2000萬粒,但從工廠工人數量和設備能力來看,潛力是很大的,如民國十三年(1924)十月份制造各種子彈340萬粒,照此計算一年有生產4000萬粒的能力。
炮彈底火、碰火,也是按陸軍部軍械司的命令,有時多,有時少。
無煙藥多時月產2萬磅,少時5千磅;棉藥坯多時月產1萬磅,少時3千磅。
產品價格:
據德縣兵工廠寅字第6799號報單開列:
七九無箭槍子每千粒價洋40元。
七九紙箭槍子每千粒價洋52.8元。
六五紙箭槍子每千粒價洋50.4元。
六五銅箭槍子每千粒價洋48元。
六五假箭槍子每千粒價洋48元。
七生五山炮木箭彈每顆價洋7.682元。
七生五陸炮木箭彈每顆價洋9.158元。(28)
五.德縣兵工廠蹤跡遺痕
德縣兵工廠平面圖
1924年,曹錕當選總統。9月24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馮玉祥倒戈,將所部改為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并于10月23日開進北京逼曹錕下臺,奉軍得以大舉南下。11月3日,曹錕宣布辭職,吳佩孚也由塘沽從海上南逃。
1925年秋,奉系軍閥張宗昌進入山東督魯,德州以南劃為其勢力范圍,德州以北則屬于奉系李景林勢力范圍。1926年2月,張宗昌下令德縣兵工廠停辦,并將機器設備拆遷至濟南新城兵工廠。原兵工廠的工人被分別遣散到濟南、漢陽、鞏縣、太原、沈陽、重慶等地兵工廠。
1937年,日軍占領德州后,在此駐扎軍隊,德縣兵工廠成為日本兵營。
抗戰勝利后,我黨為了軍事斗爭的需要,于1946年6月11日,將德州衛氏博濟醫院和博文中學校舍,連同德州火車站、德縣兵工廠一起拆除。(29)
德州著名文史學者張明福先生說:德縣兵工廠在歷史上存在22年之久,工人最多時達3000人,加之與之配套的行業,大約德州城有1.5萬人靠其生存。在清末民初戰事頻仍、災荒連發的特殊歲月,它的建立與運行,既促進了周圍失地農民和城市無業人員的就業,又極大地促進了德州地域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對德州人而言,不管袁世凱在歷史上的評價如何,兵工廠的這段歷史是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忘卻的。(30)
濟南新城兵工廠即1875年山東巡撫丁寶禎創辦的山東機械局,后更名為山東兵工廠、濟南新城兵工廠。開辦之初,因經費緊張,只好先造火藥,俟火藥造成后再造槍炮。并在興辦山東機器局的時候,所有廠房的建設和設備安裝沒有聘用一名洋匠,從光緒元年十月到光緒二年九月底,機器局的資金主要來源是:藩庫銀、糧道庫銀、臨清關稅銀,分別撥銀九萬四千兩、七萬二千八百兩、二萬兩,合:十八萬六千兩(31)。與德州兵工廠的投入相比,差距是較大的。
民國以后,山東機械局更名為山東兵工廠、濟南新城兵工廠,規模已經得到很大發展,據1914年出版的《濟南指南》稱,山東兵工廠廠內共分七處,即副官處、書記處、會計處、審計處、審格處、醫務處、差遣處;十所,即機器所、火藥所、槍子所、白藥所、煉鐵所、鑄鐵所、軋鋼所、化銅所、木工所、工程所;二庫,即物料庫和火藥庫;又附設高等藝徒教育所,學制三年。民國初年,山東兵工廠常年經費銀為13.6萬兩,改銀元后為7.4萬元(32)。投入依然很低,可見張宗昌將德州兵工廠設備遷來,對于濟南新城兵工廠意義重大。1928年4月,濟南新城兵工廠由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接管。在‘五三慘案’期間,日軍炸毀濟南新城兵工廠無影山火藥庫,劫去場內所有主要設備。濟南新城兵工廠總損失700余萬元,停產一年之久。1929年5月,改稱濟南兵工廠,主要生產‘七九’槍彈、木柄手榴彈,還曾制造過捷克式輕機槍等。抗日戰爭爆發后,濟南兵工廠主要機器設備和1000余名工人于1937年9月分14批遷往西安,改成陜西第一兵工廠籌備處,后來陸續遷往重慶等地(33)。
據山東唐氏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知名企業家唐景元2019年9月回憶說:不久前有同學去四川參加二炮戰友聚會,聯系到四川一戰友家,他家四代人從事兵工廠工作。爺爺朱玉俊(1891~1960)十幾歲就在德州兵工廠當工人,后來隨廠遷往濟南新城兵工廠。戰友的父親朱連榮跟著爺爺進了濟南兵工廠。抗日戰爭爆發,兵工廠從濟南新城遷到南京,又輾轉到重慶。建國后一段時間內遷往青海,最后落到四川綿陽。現在的名字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是生產導彈核武器的軍工企業。那個戰友轉業到四川綿陽軍工廠,侄子也在軍工廠里工作。一家三代四口從事軍工生產,可稱得上是‘軍工世家’了。
丁寶楨創辦的山東機器局,先后更名為山東兵工廠、濟南新城兵工廠、新城化工廠、山東化工廠,現為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山東北方現代化學工業有限公司。144年來此處的地理位置與軍工屬性從未改變,結構、布局也與當初基本一致,殊為難得。
天津、德州兩地文史專家學者現場考察討論
大運河德州段,昔日碼頭靜悄悄。當年有兵工廠在繁忙熱鬧。
而德州的北洋機械制造局的前世今生就沒有山東機械制造局這般幸運,它活生生地見證了民族的興衰。2019年9月,筆者在德州著名文史學者張明福、文史愛好者程磊、張偉的陪同下,考察了德州大運河和德州兵工廠遺址故地。八百畝德州兵工廠的遺址故地,有些早已成為德州市中心繁華城區的一部分了。目前該地是一處熱氣騰騰的大工地,塔吊林立、拆遷興建,一派繁忙。據唐景元回憶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及以后,在德州兵工廠遺址故地早期有航運局,棉花打包廠(兵工廠生產炮彈儲棉庫),商業倉儲(原兵工廠倉庫)、木器廠(原木樣廠)、鐵路小學(我曾在此讀書)、鐵路公寓、煤炭公司、棉麻公司宿舍、黑馬集團宿舍、航運宿舍、黑馬集團批發市場、電廠宿舍、鐵路公寓等等。在考察中我們發現,仍有一棟德州兵工廠電廠的老廠房矗立在居民小區之中。希望德州有關方面,利用該建筑,設立一座德州北洋機械局博物館,不忘初心,講好工業文明從天津擴散到德州歷史故事。
作者井振武、周醉天、唐景元合影于德州市博物館前
德州博物館中在袁世凱與德州北洋機器制造局部分的展示陳列中寫道:技術先進,產品精良,是袁世凱北洋新軍的主要武器來源之一。這是德州大機器生產的開端,標志著德州近代工業的誕生。
參考文獻:
⑴、⑵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4),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231至232頁、241頁。
⑶來新夏主編《天津近代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版,104至107頁。
⑷【英】雷穆森著 許逸凡趙地譯劉海巖校訂《天津租界史(插圖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146至147頁。
⑸【俄】德米特里·揚契維茨基著 譯者許崇信等《八國聯軍目擊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175頁至176頁。
⑹天津市河東區政協文化體育和文史委員會編《天津一局兩堂——洋務運動的北方基地》,2016年12月版,188頁。
⑺、⑻、⑼、⑽、⑾、⑿、⒀、⒁、⒂、⒅、⒆、⒇倪瑞英 趙克立趙善繼翻譯,總校訂劉海巖《八國聯軍占領實錄(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頁、10頁、99頁、52至54頁、145頁、150頁、122頁和146頁、354和358頁、706頁、625頁、688頁、757頁。
⒃張聯棻《小站練兵與北洋六鎮》,見《八十三天皇帝夢》,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12月版,187頁。
⒄馮玉祥《我的生活》(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60頁。
(18)、(19)、(20)倪瑞英 趙克立 趙善繼翻譯,總校訂劉海巖《八國聯軍占領實錄(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625頁、688頁、757頁。
(21)(《袁世凱咨民政書》)。
(22)、(23)天津市河東區政協文化體育和文史委員會編《天津一局兩堂——洋務運動的北方基地》,2016年12月版,188頁、158頁。
(24)、(25)、(27)、(28)《德州兵工廠概述》馬壽春整理,載《德州文史》第五輯,德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87年版,第135頁、第140至141頁、第137、143頁。
(26)張明福主編《德州地域文化二十講》,德州市地方史志辦公室編,2018年5月版,489至490頁。
(29)、(30)《德州往事》張明福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18、407頁。
(31)駱孝元,朱華《從山東機器局到四川機器局:丁寶楨洋務之路》,載《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年第5期,第309頁。
(32)、(33)《山東機械局尋蹤》王汗冰圖文,載《齊魯周刊》2019年6月24日封面故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責任編輯:
注明:本文章來源于互聯網,如侵權請聯系客服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