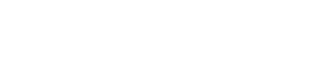山西省右玉縣善家堡墓地
原標題:山西省右玉縣善家堡墓地
山西省右玉縣善家堡墓地
《文物季刊》 1992年04期
王克林、孫春林、寧立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胡 生(右玉縣博物館)
右玉縣位于山西省北部,境內山丘連綿,峰巒起伏,植被稀疏,水土流失較為嚴重,屬晉北黃土高原的組成部分。由平魯縣發源的滄頭河(古中陵川水),蜿蜒北去,貫穿右玉縣境中部,至殺虎口出省境,經內蒙古向西注入黃河。
高墻框鄉善家堡村,地理位置為東經112°25′,北緯40°5′,南距縣城(梁家油坊鎮)約10公里,地處海拔1689米的南山西南緣,滄頭河的支流十里河由村南向西流過,呈背山面水的自然景觀。70年代初期,善家堡村民在緊靠村莊的西梁南坡,開挖一條灌溉水渠,后即廢棄,但經年累月的流水切割,形成一條寬深各十余米的沖溝,并且逐年擴大,導致溝岸土地大面積被侵蝕和塌陷。1989年春,在沖溝北側的斷壁上,村民們采集到一件雙耳銅錢,縣博物館的同志及時前往清理,又發現一件銅鑲和其它銅飾、銅幣及骨器多件,并且了解到這里以往經常有小件文物出土。依此線索,1990年5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組織雁北地區和右玉縣文物工作者,對這一地帶進行考古調查和勘探,確認這是古墓群(圖一)。從六月份開始,對探明部分進行發掘清理,歷時4個月,清理墓葬23座,出土文物413件(組),獲得了一批十分珍貴的考古學文化資料。
一、墓地與墓葬形制
墓地所在的西梁,北高南低,依山傍水。距地表約1米以上,均為質地疏松、層理不顯的典型風積黃土層,其下有不規則鈣質薄層和淡紅色粘土層。在東西長約100米,南北寬約50米的范圍內,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以東北——西南走向帶狀排布于沖溝北岸(圖二)。
許多墓葬瀕臨沖溝邊緣,或者半部已陷入沖溝,另半部尚懸掛于溝壁上。M6位于沖溝中下部,距溝岸深約5米,骨骼和隨葬品均保存尚好,當是由于溝岸土地大面積下陷而所致。可以斷定,由于這種大面積坍塌,被毀壞墓葬自然不在少數。另六一些墓葬墓穴很淺,由于水土流失和農田耕作等原因,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暴露于地表。
為了全面揭露墓地的文化內涵,我們在鉆探資料的基礎上,開了10×10米探方13 個,但除幕葬之外,沒有發現其它文化層堆積。少數嘉葬較深,建于淡紅色粘土層中,形狀結構十分清楚,為典型的長方形土壙豎穴墓。絕大多數墓葬距地表很淺,墓壙土和墓室填土均為黃砂土,土質土色較為一致,很難區分。根據人骨架和隨葬品排列放置狀況,對比、叁照四邊清晰的墓葬結構形態,我們完全可以肯定,這些墓葬也是長方形土壙豎穴墓。
23座墓葬中,沒有發現任何葬具痕跡,依葬俗不同,可分為單人葬、合葬和叁考墓葬三類,下面分別予以介紹。
(一) 單人墓葬 共計15座,其中兒童嘉1座,成人墓14座。
1、兒童墓 1座(M19),墓壙儂土色,可推知為長方形土壙豎穴墓,墓底長約1.2、寬0.5、深約0.3米,方向307°。人骨架腐朽殘缺,但大部分尚存,為一年齡約十歲左右的兒童,身高1-1.1米,仰身直肢,面向上,無任何隨葬品(圖三)。
2、成人墓 14座 墓形基本一致,深淺略有不同,個別墓設有小龕。
M4 墓壙不明顯,長約1,9、寬約0.8、深0.7米,方向315°。人骨朽毀嚴重,僅有部分頭骨和肢骨,故葬式、年齡 和 性 別不明。頭前部挖一深0.45米的小坑,大小僅容胸瞳1件;軀干旁置陶碗1、陶罐1,骨盆旁放雙耳小罐1,足部有殘鐵器1件。
M6 發掘時已下陷至沖溝半壁,由于塌方面積較大,對墓葬沒有形成嚴重破壞。四壙不明顯,深約0.6米,方向約285°。人骨粲仰身直肢,面向北,男性。隨葬品集中在究者頭骨和軀干部位,主要有小銅杯1、陶罐1、玉飾件2、鐵鏃、鐵環和殘鐵器等(圖四)。
M9 墓壙不明顯,依痕跡 知 其 長約2.05、寬約0.8、深約0.3米,方向308°。死者身體微側,直肢,面向上,男性。在頭骨右上部放置陶罐1件,其它隨葬品多集中于軀干周圍,主要有玉(瑪瑙)飾件、銅帶扣、鐵刀、鐵削及鞘、鐵剪、陶杯和羊矩骨等(圖五)。
M11· 墓壙不明顯,約長1.9、寬0.7、深1.26米,方向326°。人骨架保存較好,男性,側身直肢。頭前隨葬一件陶罐,罐上壓一塊不規則石塊,其它有銅指環和玉飾器。另在墓室中層填土中,出有陶罐一件和部分殘骨。
M15 墓西、南兩邊壙較清晰,北、東兩邊壙不顯,長約1.9、寬0.7、深約0.6米,方向310°。人骨架保存較完整,面向上,側身直肢,女性。隨葬品集中在頭部和身軀兩旁,頭北側置鐵鑲1件,身旁主要有銅帶扣、鐵鏃頭、陶杯和羊矩骨等(圖六)。M17 墓壙不清,長約1.9、寬0.8、深0.8米,方向315°。骨架保存較完整,男性,仰身直肢,隨葬品以生活用具、兵器和骨角器為主,頭側置陶罐1件,身邊有小銅杯1 件,還有鐵剪頭和骨角器等,腿部有鐵矛(失柄)等兵器(圖七)。
M18 墓壙不明顯,長約1.7、寬0.85、距地表深1米,方向313°。身軀略側,四肢微屈,面向東北,為中年男性。隨葬器物比較豐富,多達50多件,其中包括鐵馬具、鐵帶飾、鐵刃銅鏟、鐵鋤(?)、鐵刀、銅飾件、玉飾件以及骨針等許多骨角器和裝飾品(圖八)。
(二)合葬墓 共計5座,分成人與兒童合葬和男女雙人合葬兩種情況。
1、成人與兒童合葬墓 2座。其中,M2上部邊壙不清,上層填土中有許多散亂的磚塊,磚下壓著一具兒童頭骨和一段殘肢骨,頭骨亦已破碎,性別不明,在其西側置陶罐1件和綠松石串飾1件。下部邊壙清晰可見,長2、寬0.8米,方向300°。在距地表1.45米處為墓底,埋葬一名成年男性死者,仰身直肢,身邊無隨葬器物,只在股骨旁有少許動物骨骼。在成人與兒童之間的填土中,發現一對對稱的弧狀骨器。又如M 16,墓壙不清,方向約310°,隨葬分上下兩層上層為一兒童殘骨,性別不辨,隨葬陶罐兩件和鹿矩骨等下層為男女成人合葬,北側男性位置靠下,南側女性較男性靠上,皆仰身直肢,骨架保存較完整。女性死者頭旁置陶罐2件,礪石1,身邊有瑪瑙串飾、銅指環、殘鐵器,腳邊亦有陶罐1件男性頭邊發現銅飾和瑪瑙牢飾,身邊有制作精致的骨器和殘鐵器,足下隨葬鐵鍍1件。另外,在填土中發現綠松石管狀串飾1件。這種成年男女和兒童三人共葬一墓的現象,在這片墓地中僅此一例(圖九)。
2、男女雙人合葬墓3座 墓形與單人葬者相同,皆為長方形土壙豎穴。
M1 位于墓群西端,墓室上口已被耕作破壞。墓壁清晰整齊,上層為耕土和黃沙土,下層為淡紅色粘土,長2.28、寬1.25、深1.6米,方向300°。墓底平坦。人骨架二具,北側男性,腐朽散亂嚴重,隨葬品豐富,有銅鑲1件、鐵刀1、鐵鏢1、鐵斧1、鐵錘1,鐵箭頭以及殘金箔牌飾,小銅罐1件、鐵腰帶和其它銅飾件;南側女性,骨架保存完整,仰身直肢,頭上部置銅鑷1、小銅杯1、石器1,銅盆旁有銅帶扣和鐵削刀等(圖十)。
M3 墓室北、南二壁清晰 可見,但東、西二壙不明。依遺跡判斷,知西壁較東壁略寬,墓室平面大致為梯形,長約2.7、寬約1.1~1.3、深1.35米,方向285°。人骨架二具,均保存較好,仰身直肢,面向上。北側者男性,位置靠下,隨葬品僅為瑪瑙串飾、銀指環和鐵駑箭桿等,南側女性,位置較靠上,隨葬品較多,主要有陶罐2,瑪瑙(玉)串飾1組,金箔飾(殘)1,銅釧、鐵削刀、銅管狀飾和殘漆器等。在墓底近西壁處挖一直徑約0.3米的小坑,深0.35米,內置1件陶罐;兩具人骨架的下肢和足部,都有一些獸骨,當為殉牲遺跡(圖十一)。
M5邊壙不清,長約1.9、寬約0.8、深0.75米,方向290°。人骨架二具,皆仰身直肢,部分骨骼散亂。南側女性,北側男性,二人身首緊緊靠攏,男性的部分身軀迭壓于女性身軀之下。女性一側隨葬品略少。頭前有陶罐1件,身邊有銅飾、殘鐵器、骨器和瑪瑙串飾男性隨葬品略多,主要是銅帶扣、鐵剪、金牌飾、金箔飾件和瑪瑙、蚌珠等組成的串飾(圖十二)。
(三)叁考墓 3座,這類墓葬墓壙不清,未發現任何人骨,只有一些隨葬器物,排列也無規律。我們在這里無法推斷其原因(如被遷葬等),姑將其作為叁考墓葬處理。二、出土器物該墓地出北器物總計413件,其中包括無墓葬單位的采集品72件,它們分別為陶、銅、鐵、金銀、骨角、玉石、漆木等不同質地的制品。
(一)陶器30件,主要有罐、碗、杯等幾種。
1、夾沙灰褐陶罐,19件。依其造型不同,又可分為5型。
I型 12件 灰褐色夾粗砂胎,大口、平底、體疲長,手制,頸部飾戳刺紋。如
標本M3∶1,手制,火候低,表面粗糙。口微侈,斜肩,折腹,平底。頸部戳刺一周不規則指甲紋。口徑12、腹徑18.7、底徑13.8、高27.8厘米(圖十三,1圖版壹,1)。
標本M21∶1,口微侈,斜方唇,腹微鼓,頸飾一周篦點狀錐刺紋,器表粗糙。口徑16.5、腹徑20、底徑11.7、高26.4厘米(圖十三,2)。
標本M5∶1,手制,火候較低,大口外侈,腹微鼓,小平底,表面較粗糙并殘留煙食。在頸部飾篦點狀戳刺紋,下腹部有豎向抹壓痕。口徑13、腹徑13.4、底徑6、高17.6厘米(圖十三,3)。
標本M22∶1,大口,卷沿,圓唇,腹稍外鼓,小平底。頸部飾篦點狀 錐 刺 紋一周。該器燒制火候較低,部分呈紅或白色,表面粗糙,布滿煙食。口徑15、腹徑15.5、底徑7.8,高18.5厘米(圖十三,4圖版壹,2)。
標本M3∶3,手制,器表粗糙,口外侈,方唇,束頸,上腹微鼓,下腹內收,平底,頸部施兩周戳刺紋。口徑13.7、腹徑17.6、底徑8.4、高16厘米(圖十三,5圖版壹,3)。
標本C1(采集),手制,火候低,部分呈紅色,器表布滿煙食。口外侈,卷沿,圓唇,頸較細長,腹較圓鼓,平底,肩飾一周不規則指甲紋。口徑12、腹徑18、底徑10.5、高23.5厘米(圖十三,6)。
標本M13∶4,火候低,部分呈暗紅色,表面粗糙,侈口,卷沿,圓唇,束頸圓腹,平底內凹,肩頸交接處施一周戳刺紋。整體器形為方形,高寬相若。口頸10.8、腹徑15.5、底徑8.7、高15.6厘米(圖十三,7)。
標本M11∶1,多口,卷沿,圓唇,頸較長,腹鼓圓,下部內收,狀若圈足,頸部施二周篦點狀戳刺紋。口徑10.8、腹徑15.2、底徑7.5、高19厘米(圖十三,8)。
Ⅱ型 2件 整體造型與I型相近,素面無紋。如∶
標本M2∶1,手制,火候較低,表面粗糙,布滿煙食。侈口,圓唇,體較瘦長,腹微鼓,平底,素面。口徑9.8、腹徑13、底徑7.8、高18.7厘米(圖十三,9)。
標本M11∶5,手制,不甚規則,表面粗糙,無紋,布滿煙食。侈口,圓唇,束碩,折腹,平底,腹壁斜直。口徑12.3、腹經16.5、底徑9.3、高18.5厘米(圖十四)1)。
3型 1件(標本M20∶1)。手制,表面粗糙,殘留煙食。廣口,斜方唇,腹微鼓,下部內收,平底。頸部附加一道凸棱帶,棱帶上再施戳刺紋。口徑16.8、腹徑17.5、底徑10、高20.4厘米(圖十四,2號圖版壹,4)。
Ⅳ型 2件,造型與I型相類,只在腹部附加四個鼻形二。如∶
標本M17∶1,夾砂灰褐陶,手制,表面粗糙,有裂痕,布滿煙臭。體瘦長,敞口,卷沿,圓唇,頸部施不規則篦點狀戳刺紋,肩部附加四個對稱的鼻形濕。口徑17.4,腹徑18、底徑9.9、高24厘米(圖十四)3;圖版壹,5)。
標本M4∶2,口沿寬厚,近盤形,稍微外侈,方唇,下緣施戳刺紋。體較短粗,腹部附加四個對稱的鼻形濕。口徑13.6、腹徑14、底徑8.1、高15.6厘米(圖十四)8;圖版壹,6)。
V型 1件(標本M 4∶3),夾砂灰褐陶,手制,表面經打磨而現出光澤。侈口,卷沿,圓唇,鼓腹,平底,口沿下和肩部分別施一周或二周戳刺紋,腹下部內收,狀若假圈足。肩頸部安裝兩個對稱的橋形耳。該器高度和寬度適中,造型別致。口徑6、腹徑8、底徑4.5、高8.1厘米(圖十四,5圖板貳,1)。
2、泥質灰陶罐7件。依其形狀大致分為3型。
I型 2件。器短寬,大底。如標本M3∶2,侈口,卷沿,圓唇,溜肩,鼓腹,大平底。燒制火候較低,表面粗糙,無紋飾,肩部留有輪制的弦紋痕跡。口徑8、腹徑12.8、底徑8.5、高12.1厘米(圖十四;6;圖版貳;2)。
標本M4∶5,泥質灰陶,輪制。口微殘,寬平沿,圓唇,直頸,鼓腹,大平底,肩部飾兩周凹弦紋,弦紋之上分飾內凹水波紋。該器在腹中部一裂為二,沿裂口錐五對對應的小孔,顯系用繩綴合之用。口徑13.5,腹徑28.6、底徑21、高24.6厘米(圖十四,4)。
I型 3件。器型高六于寬。標本M16∶8,輪絹,小口,束頸,溜肩,鼓腹,平底,肩部留有輪割弦紋痕,表面剝蝕嚴重。口徑7、腹徑16.2、底徑9.6、高19.8厘米(圖十四,7圖版貳,3)。
標本M10∶1,輪制,侈口,卷沿圓唇,卵形腹,平底。肩部飾凹弦紋一周,弦紋往下至底模壓細密的三角形紋帶19周。器失底,裂口處綴合用小鉆孔,可知原曾修復。口徑14.4、腹徑24.8、底徑13.2、高29.7厘米(圖版貳,4)。
Ⅱ型 2件,體扁寬,短直頸。標本C∶2(采集),泥質灰陶,輪制,下部殘留轉輪痕跡,火候較低,剝蝕嚴重,素面。口徑11、腹徑19.5、底徑9.7、高17.2厘米(圖十四,9圖版貳,5)。
標本M10∶3,泥質灰陶,輪制,敞口,束頸,鼓腹,平底,肩上部施多方連續性麥穗紋一周。口徑10.8、腹徑17、底徑10.2、高14.5匝米(圖十四,10圖版貳,6)。
3、杯 2件,夾砂灰陶,手制。
標本M9∶13,制作粗糙,不規整,壁斜直,大口,圈足外撒。口徑5、底徑3.1、高4.7厘米(圖十四,11)。
標本M15∶11,火候不高,灰色中夾雜淡紅色,器形不規整。大口,斜直壁,平底,內底近錐形,口徑5.3、底徑2.4、高4.4厘米。
4、碗 1件(標本M 4 1),泥質灰陶,輪制,敞口,圓唇,折腹,假圈足,腹部有三道輪制弦紋。口徑15、底徑6、高6厘米(圖十四,12)。
(二)銅器共計96件,其中采集38 件,種類有容器、酒器、工具、兵器、裝飾品、日常用具和各種飾件等。
1、錢 3件,圓筒狀,平底,雙耳。標本M1∶8,大口,腹微外鼓,平底。口上有兩個對稱的橋狀耳,耳面內凹,耳下順口部有一道凸弦紋,弦紋之下飾四組弧形紋。口徑11.2、腹徑12.4、底徑8.2、通高17厘米(圖十五,1圖版叁,2)。
標本C∶3,體短寬,約呈方形,大口,卷沿,圓唇,鼓腹,平底。口外側立兩個扁平的鈕狀耳,耳面弧凸,呈弧形向腹部延伸,一耳殘。與口沿平行也有一道凸弦紋,橫過耳之伸延弧線。口徑16.8、腹徑19.8、底徑12、通高21厘米(圖十五,2)。
標本C∶4,口沿呈帶狀,敞口,圓唇,體較瘦 高,平 底。口 外側立兩個紐狀耳,耳面內凹,兩緣凸出,呈弧形向腹部延伸,口徑15.5、腹徑17.4、底徑9.3、通高22.5厘米(圖十五,3圖版叁,1)。
2、罐 2件,形制各異。
標本M1∶2,侈口,圓唇,短頸,鼓腹近球形,下腹近底處內凹,狀若假圈足。肩部橫置一橋形紐。器體銹蝕嚴重,腹部有兩個圓形鉚釘,一大一小,應為當時修補遺跡。口徑3.8、腹徑5.5、底徑3.3、高6.4厘米(圖十五,4圖十八,3)。
標本C5,直口,圓唇,矮頸,深腹,平底,肩部橫置一環狀紐。口微殘。口徑3.2、腹徑4.8、底徑2.8、高5.5厘米(圖十五,5圖版叁,6)。
3、杯 2件
標本M17∶12,口內折,弧腹,平底,圈足。近口沿處橫裝一個環形墨耳,素面無紋。口徑5.5、腹徑6、底徑3.6、高4.8厘米(圖十六,1圖十九,12)。
標本M6∶2,大口,弧腹,平底,近口處橫置一個環狀寫,素面無 紋。口徑4.2、腹徑4.4、底徑2.8、高4.1厘米(圖十六,2圖十八,1)。
4、壺形器 1件(標本M1∶18),直口,鼓腹、圈底,上腹部接一長方形流。器表附著銅銹和鐵銹,口微損。口徑4.5、腹徑8.5、通高5.5厘米(圖十六,3 圖十九,3)。
5、勺 1件(標本M18∶24),球形腹,髓底,口沿磨損不齊,向上延伸出一耳狀飾,中有小孔,應為鉚接勺柄之用。柄已失。口徑7.6、勺高3.4厘米。
6、鐵刃銅鏟 1件(標本M18∶14),鏟質,半圓形,兩側有凸起的邊部上部為扁方形裂,瓷口為梯形,下部背面用四個鐵鉚釘聯接長方形鐵刃,刃長3.9、寬9厘米鏟通高10.1厘米(圖十六,6圖版叁,7)。
7、帶扣 12件,依形制與結構不同,可分五型。
I型 1件(標本M5 ∶8)。橢圓形,帶紐上方伸出兩個對應的弧狀鉤,一鉤已殘缺。通長4.4、寬3.4厘米,
Ⅱ型 4件。形狀基本相同,大小不一,M15∶14,上部心形,由心尖下弧并向內彎成對應雙鉤,下接凹形欄以為帶紐,紐上附著朽帶。通長3、寬2.6厘米(圖十九,8)。
Ⅲ型 1件(標本M15∶3)。整體結構與Ⅰ型相似,唯將雙鉤轉而內折,連接成塔形。長3.8、寬3.5厘米(圖版叁,4)。
Ⅳ型 1件(標本C∶6)。扣環兩側裝飾成龍鳳紋,尾部相交成鉤突,爪部接紐,正面陰刻龍鳳細部紋飾,五官、羽鱗等神態逼真,栩栩如生,通長4、寬3.5厘米(圖十六,4圖版卷,3)。
Ⅴ型 4件。形式基本相同,其中兩件缺扣環。標本M9∶7和M9∶12,用厚約0.1厘米的銅片截成,橢圓形環,長方形紐。紐上接一個帶鼻紐的方形帶飾,帶飾鏤空成花瓣形,前后兩個鉚釘與皮帶相結。通長5.6厘米(圖十六,5圖十八,7)。
8、釧 4件。多數已殘,直徑在6~7厘米之間;斷面不規則圓形。直徑 約0.3 厘米。
9、指環 6件,用銅絲盤 繞 數 周而成。
標本M8 ∶5,用兩端尖銳的銅絲對繞一周半而成,直徑2厘米(圖十八,5)。
標本M16∶11,用直徑0.2厘米的銅絲盤繞四周,狀若今之彈簧,出土時尚套在指骨上。直徑2.1厘米(圖十八,2)
10、鏡 1件(標才M8 2)。大部殘缺,僅余一小部分。內向連弧紋,外是寬平緣,斜唇,表面光潔無銹痕(圖十九,7)。
11、鑷 1件(標本M1∶1)。用兩片完全相同的扁銅片對合而成,前端扁寬,后端窄圓合成環狀,中間套兩個銅箍,后箍固定不動,前箍可前后推移,用以控制鑷尖的張合程度,通長9.1厘米(圖十七,1圖版叁,9)。
12、飾件 1件。上部圓筒形,下部截成不規則花瓣狀并外撇,花瓣邊緣有三個用以縫綴的小孔,通高4厘米。
13、管狀飾 2種。一種是用十多個小銅環串聯而成,另一種為銅絲盤繞而成,狀若彈簧。
14、鹿頭飾 1件(標本C∶7)。用銅鑄成鹿頭形,厚約0.15厘米,中空。在鹿耳和腮部鉆小孔,估計其為縫綴在身上的飾物(圖版叁,10)。
15、人形垂飾 1件(標本C∶8)。男性,裸體,圓臉,矮鼻,雙手持物置于胸前,腿微屈,腳被繩索捆縛。頭頂接一個環狀小紐,用以懸掛。通高6.4厘米(圖十七,2 圖版肆,9)。
16、鏇 1件。標本M17∶19,斷面三棱形,鋒尖銳利,刃弧形,關后接鐵鋌。鋌殘缺,僅有斷痕。長3.7厘米(圖十七,3)。
17、錢幣 5枚,其中三枚為采集品。標本M1∶9 最為完整、清晰,錢徑2.3、郭徑2.5、穿寬1厘米,五字兩筆曲折,朱字頭彎曲并高于金字(圖二十)。
18、其它 除上述銅器外,尚有幾種飾件,如環、帽形飾和蒜頭形飾等,從略。
(三)金器 12件,包括牌飾和其它飾件。
1、脾飾 2件,金箔錘蝶而成,均已殘缺。
標本M5∶14;僅存原牌飾之半;中心飾佇立的鹿。鹿作回首狀,頭上有圓形鏤空,表示鹿角,邊框飾兩周繩索紋。殘長4.4、寬5.8厘米(圖十七,4圖版肆,10)。
標本M5∶13,殘損嚴重,中間動物紋已無法辨認,邊框飾繩索紋兩周。
2、馬形飾 1件(標本M1∶17)。由一殘金飾改制而成,體現了側立馬匹的輪廓和神態,下部鉆有小孔,多為縫綴之用(圖版叁,8)。
3、條形飾 2件,用金箔 裁 出 長條形,素面無紋,沿邊緣有針眼。
4、泡飾 7件,形制相同,用圓形金箔錘成泡狀,周邊有針孔,尺寸在1.1~1.4 厘米之間。該飾件出土于M1死者頭頂部,疑為冠飾(圖十九,6)。
(四)鐵器 77件,其中采集品3件。個別器物因銹蝕嚴重,殘碎不堪,器形難辨。
1、鑲 2件,形制不同。
標本M15∶1,桶狀,口大 底 小,平底,口沿上立兩個紐狀耳(缺一),銹蝕嚴重。口徑16.5、底徑9、通高17.8厘米(圖十九,9)。
標本M16∶5,口微斂,球形腹,外底有斷痕,原應有圈足。口沿上有兩個寬大的耳,外緣凸出于鑲口,耳高內凹。表面銹蝕嚴重,澆鑄合范痕跡清楚。口徑10、通高14 厘米(圖十七,5圖十八,6)。2、斧 2件,分為二型
Ⅰ型 1件(標本M1∶25),平面梯形,側面三角形,斷面長方形,從側面橫開長方形裂口,刃寬5.8、通長9厘米(圖十七,6)。
Ⅱ型 1件(標本M17∶16)。正面長方形,側面三角形,一端為寬刃,另一端開長方形釜口。通長5.8、刃寬5.5厘米(圖十七,8圖十八,4)。
3、錘頭 1件(標本M1∶27)。平面長方形,側面近梯形。兩端均為打擊平面,上端較小,下端較大。從側面橫開長方形鑒口。長5、寬2.3厘米(圖十七,7)。
4、鋤 1件(標本M18∶32)。平面梯形,側面三角形,上端殘缺,刃端寬大∶通長約8、刃寬10厘米(圖十七,9)。
5、刀 14件,分為二型
I型 長刀類,4件,最長68厘米,最短29.5厘米。
標本M9∶10,環首,直背,斷面三角形,刀與柄無明顯界限,刀身銹蝕嚴重,附著木痕。通長68、寬3.8厘米(圖二十一;1圖版肆,4)。
標本M1∶21,一字形首,柄扁平,外包木質,窄于刀。刀由前向后漸寬,斷面三角形。原插于木鞘內,鞘已朽。通長40厘米(圖二十一,2圖版肆,7)。
標本M18∶31,刀背平直;刀柄扁條形,刀身橫斷面為三角形,柄部附有朽木。通長38、寬22厘米(圖二十一,3)。
Ⅱ型 長刀類 10件,形制與標本M18 ∶31大致相同,刀身較短。標本M1∶20,殘長17.2厘米;標本M8∶1,殘長10.5厘米。
6、矛 4件,分為二型Ⅰ型 2件 形制基本相同。
標本M1∶6,銹蝕嚴重,中脊不顯,斷面約為菱形,骸為圈筒式,上小下火,鍛造合縫清晰。通長31,散蛩口直徑約2.8厘米(圖二十一,4圖版肆,8)。24. 標本M17∶8形狀與M1∶6相同,略小。通長26厘米(圖十九,4)圖二十一,5)。
冒型 2件,細長錐狀,斷面圓形,中空,斷端為蛩口。該器有如今之標槍頭,暫歸矛類。標本M1∶22,通長39.6厘米(圖二十一,6圖版肆,6)。7、鐵鏃 17件,分為二型。· Ⅰ型 2件,形狀大致相同,標本M1 ∶28,前鋒圓鈍,兩刃突起,中脊明顯,兩翼窄長。關扁寬,中有脊棱,連接木鋌。通長8.5、寬3.9厘米(圖版叁,5)。
Ⅱ型 15件,平面、斷面均為菱形,銹蝕較重,鐵鋌外包木質。標本M43∶11,殘長6.8厘米。
8、腰帶飾 1組(16件)。標本M1 ∶19,將平面長方形、斷面微鼓的鐵質帶飾一字排列,釘于背面的皮麻質類腰帶上,帶飾下接壁形鐵環。因銹蝕嚴重,帶飾的花紋以及細部結構不明(圖十八,8)。
9、馬銜 1件(標本M18∶7)。兩節直棍式,兩端兩個大環,中間有兩個小環相套。
10、帶卡 1件(標本M18∶3)。圓角長方形卡圈,卡針直接安在卡圈短邊上。通長約6.8、寬5.3厘米。
11、剪 1件,標本M9∶14,因銹蝕嚴重,已殘缺,但形狀尚可識別。
(五)骨角器 共計41件(采集品3 件)。其中一部分為生活用具,另一部分為裝飾品。
1、鏟形器 1件(標本M16∶2)。平面鏟形,弧臂,橢圓形首,長條形把。首部以中線為軸,兩側對稱線刻兩具幾何形虎紋,虎身飾網格紋,把中脊凸起,兩邊鉆對稱3組小孔,孔內尚殘存銹蝕的鐵鉚釘,可見原來尚有其它附件。柄寬2.5、首最寬處5、通長21厘米(圖二十一,7)圖版肆,3)。
2、舟形器 2件 用鹿的彎角琢磨而成,二器形制基本相同,但不知何用。,十
標本M17∶15,器前部為彎鉤狀首,斷面近方形,尖端鉆一小孔后部為獨木舟形,從上面開口,中心挖空,斷面呈凹形。在凹槽的最前端底部,鉆一小孔。通長19.5 厘米(圖二十二,1圖版肆,2)。
標本C∶9,結構與M17∶15相同,前部彎曲尖端有孔,斷面呈橢圓形后部斷面為U形。通長20.5厘米(圖二.十二,2圖版肆,1)。
3、圈點紋骨飾 2件,用動物長骨剖制而成,由一側挖空使之成為凹形,將器表磨成五個棱面,每棱面陰刻圈點紋。標本M 18∶17∶長14,2、寬1.7厘米,每行圈點紋18 ~23個不等,一端附著鐵銹(圖版肆,5);標本M1∶24,殘長7厘米。
4、弧形器,2組4件,略呈弧形,斷面半月形,一端較寬,側面磨有半圓形缺口,沿缺口常有繩索磨擦的凹痕另一端較細長。該器成雙出土,兩兩對稱,可見其為同時使用。標本M2∶2,殘長18.5厘米(圖二十二,3);標本C∶10,長29.6厘米(圖十九,5圖二十二,4)。
5、針 1件(標本M18∶10),細長錐形,斷面略呈扁方形,前端較尖銳,后端有穿線(繩)的冠孔。器表有磨擦痕。長4.5 厘米(圖十九,10圖二十二,7)
6、觴 1件(標本M18∶16),用動物角制成,錐形,未加仔細雕琢,微弧,表面粗糙,斷面圓形,尖端銳,后端圓鈍。長16.9厘米(圖二十二 5)。
7、柳葉狀飾 3件。標本C∶11,用動物長骨切割、磨制而成,柳葉形,邊緣磨。成刃狀,斷面微弧,中間寬,兩端銳利,一端鉆有小孔。長25.3、最寬處3.3厘米。
8、管狀器 1件(標本M17∶2)。用動物肢骨加工而成,一端為關節頭,另一端為口,器口磨成斜邊。器為中空的管筒狀,可能為小型日用容器,長10.3、外徑1 厘米。
9、長條形器 2件,扁條狀。標本M 19∶4,殘損,斷面略呈梯形或半圓形,中部高窄,邊端低寬。殘長8.8厘米。
1件(標本M18∶15)。
10、羊角飾
用羊角和部分頭骨加工而成,圓形底,上安二角。圓底沿骨縫斷裂為二,沿邊緣鉆四組八孔,每二孔相互對應,當為連 綴加固之用。通高11厘米(圖版肆,11)。
11、菱形飾 2件。略呈菱形,中間開孔,斷面扁平。標本M18∶39,長4、寬2 厘米(圖十九,11)。標本M18∶12,稍殘,長3.8、寬2.1厘米。
12、弧形飾 1件(標本M15∶4)。一側外弧,另一側為二個連續的小弧,斷面扁平,中間有一小孔。長3厘米。
13、餅狀飾 3件,用髕骨磨制加工而成,平面為不規則圓形,正面微凸,底面內凹或平,有一件中心有穿孔。
14、羊矩骨 6件,用矩骨略作加工,鉆孔。
15、鹿角飾 3件。標本M18∶37,為管狀飾,截取鹿角一段略作琢磨,中空,斷面環形。長1.9、外徑3.1厘米。標本M18∶27,用一段鹿角,將其兩端切割修整,約成橢圓形。長6厘米。標本M17∶4,Y狀,有人工切割痕,長13厘米。
(六)玉石器 153件(含采集57件),其中包括玉、石、瑪瑙料器等制作的各種器具和裝飾品。
1、礪石 1件(標本M18∶11)。青灰色花崗巖質,束腰銀錠狀,正面有五道平行凹槽,兩側為磨礪面,已成內凹的弧形。窄端寬4、寬端寬4.9、厚2厘米(圖十九,1)。
2、棒形石器 2件。標本M1∶23,灰色頁巖質,長棒形,斷面略呈橢圓形,稍厚一端鉆小孔,內有殘斷的鐵質。長13.1厘米(圖二十二,6)。標本C∶12,黑色燧石質,略短,鉆有一小孔,長4.5厘米。3、其它石塊 8件,采用天然石塊作少量加工,有的略經磨光,形狀不規則,用途不明。標本M1∶3,褐色青石質,平面為不規則五邊形;斷面扁平;長11.2、寬8.5、厚1.5厘米;標本M18∶23,為一塊小鵝卵石之半,一端有磨擦痕,較平整,長3.8、寬4.3厘米。
4、玉蘭 1件(標本M18∶21)。淡綠色硬玉,表面光潔品瑩,彎刀狀,一端尖銳,另一端圓鈍,鉆一小孔,斷面扁平,長9.7厘米(圖十九,2圖二十二,8)。
5、串飾 141件,其中采集26件,質料分瑪瑙、綠松石、琉璃等,一般綠松石質串飾的體形較大;瑪瑙和琉璃質者形體較小,顏色有暗紅、桔紅、橙黃、藍、綠赭等。
珠類串飾有圓形、扁圓形、瓜棱形、八面棱形等幾種管類串飾有圓形長管、圓形短管、半圓形、扁六棱形等數種(圖十八,9)。
(七)其它
1、殘漆器 1件(標本M3∶16)。腐朽殘毀,器形不明,漆皮一面鬃朱紅漆,另一面為黑色,與金牌飾同出。
2、蚌珠 3件。風化易損,用蚌殼磨制而成,直徑0.6~0.8厘米之間。
三、初步認識
善家堡出土的這批墓葬,分布集中,排列有序,墓葬形制結構一致,出土遺物面貌特征清楚,是一批十分重要的考古學文化遺存。
一、長方形土壙豎穴墓,是中原地區從新石器時代以來,一直延續使用的墓葬類型之一,同時,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最主要的墓葬形態,在春秋至漢唐之際更是如此。
二、善家堡墓地出土的器物,主要有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銅器、工具、兵器和裝飾品。夾砂大口平底罐用作炊具,泥質罐多用作容器,這與內蒙古札賚諾爾墓地、吉林榆樹縣老河深墓地基本相同;兵器和其它器具品種多樣,如刀、矛、斧、腰帶、鍍等,一反春秋戰國時期以銅為主要質料的特點,進而變為鐵制品,這是我國北方地區到漢代才出現的重要文化特色。銅鏡殘片具有東漢后期長宜子孫鏡的鮮明造型特征,五銖銅錢也顯示出東漢桓帝前后的時代風格。因此,我們初步認定,善家堡墓地的上限不早于東漢后期桓靈之際,下限約當魏晉時期。
三、善家堡墓地的出土器物,與中原同時期漢族文物相比,無論從種類方面,還是從造型特征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異。而與內蒙古東部、東北地區和鄂爾多斯地區出土的匈奴文化及鮮卑文化相比,卻表現出強烈的共性,反映了較為一致的文化背景、生產和生活方式。夾砂大口戳刺紋罐,是內蒙古完工、札賚諾爾、嘎仙洞石室、南楊家營子、伊敏東站、孟根楚魯墓地和吉林榆樹老河深墓地最具代表性的陶器,它們大多被用作炊具,器表常常殘留煙食。這些兩漢時代的墓葬遺存,經過多年來的探索和論證,現已基本得出共識,確定它們為漢代鮮卑族文化遺存。另外,在今呼和浩特市一帶出土的北魏墓葬,特別是大同市電焊器材廠墓地出土的北魏陶器,從始至終都普遍流行大口夾砂戳刺紋罐。無庸諱言,這些遺存存在著種族和文化意義上的相互影響與傳承關系。
兵器和裝飾品通常是鮮明的民族標志。善家堡墓葬出土的鐵刀、鐵矛、弧形骨器以及各種形狀的串飾,大多不見于同時期其它民族的文物中,而目前尚不明用途的弧形骨器更只發現于完工、札賚諾爾、南楊家營和大同市北魏時期鮮卑墓葬中,這種小型器具往往世代相傳而不為他族所用。善家堡的銅帶扣,造型結構獨特,目前亦只在札賚諾爾和大同發現了類似的標本。
四、鮮卑是源于東胡族的游牧民族,《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服虔云∶東胡、烏桓之先,后為鮮卑,鮮卑不為文字,刻木記契而已,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日"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到目前為止,我國北方歷史上的東胡、匈奴文化遺存,只在內蒙古伊盟西溝畔發現一處,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草原游牧民族文化遺存以墓葬形式出現,而絕少遺址,善家堡鮮卑文化亦不例外。雙耳銅(鐵)便于攜帶,骨角器在日用器具中居多,兵器、工具和少量農具以鐵質為主,破裂的陶容器修復后繼續使用,這一方面印證了文獻中鮮卑族以游獵為主的經濟生活和習俗,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在南遷過程中,生產力水平仍然較為低下的客觀狀況。
五、右玉古稱善無,其故城遺址即今右玉城鎮,殘毀的城垣及瓦礫尚在。善無自古即為通塞大道之要沖,東鄰平城,南接中陵,往北經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進入大漠。西漢時為雁門郡治所,東漢郡縣南徙,又為定襄郡治。雁門、定襄均隸屬并州刺史部。東漢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此故地。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余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轉盛。此后,緣邊郡縣多與鮮卑相接,到三國時,善無等地更為鮮卑所據,因而戰事頻繁。延光元年冬,鮮卑寇雁門、定襄、太原寧壽二年,檀石槐攻云中延熹二年,攻雁門,又攻遼東;熹平二年;攻幽、并二州;并連年不斷。曹魏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強盛,屢擾幽并,次年被并州刺史梁習大破之。甘露三年,拓跋部大人力微居定襄之盛東,景元二年并遣子至洛陽貢獻。在這種戰爭與和平、動蕩與交融相互作用的社會大背景下,善無成為了多民族活動的大舞臺,因而善家堡墓地的文化面貌表現出以鮮卑文化特征為主,兼容匈奴文化和漢族文化因素的多元共存的鮮明色彩。
叁加發掘的同志有∶孫春林、胡生、王守平、王志輝、胡春明、寧立新、王克林等同志,雁北地區文物工作站張暢耕、劉俊喜、左雁先生曾給予大力支持,謹致感謝。
攝影:李建生,
繪圖:李碧、暢紅霞
溫馨說明:本平臺目的在于集中傳遞全國各縣考古成果,不作為任何商業目的,轉載請注明出處。我們敬重和感謝原創作者,凡未注明作者姓名的文章,均因無法查獲作者所致,敬請原作者諒解!如有涉及版權問題,敬請原作者或同行告知,我們將及時糾正刪除。圖文編輯校對過程中難免出現錯誤,敬請讀者批評指正,我們將及時糾正修改。謝謝合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責任編輯:
注明:本文章來源于互聯網,如侵權請聯系客服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