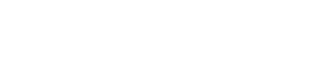“仙人乘槎”與“張騫乘槎”形象演變
原標題:仙人乘槎與張騫乘槎形象演變
原作者:高超
注意!!!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蘇州吳中博物館藏有一設計精巧,造型奇特的銀槎 (圖一),槎杯使用白銀制成,整器斜長22厘米,寬約7.5厘米,高11.4厘米,腹空。槎的背尾陰刻至正乙酉朱碧山造八個銘文 (圖二),可知該器為公元1345年元代銀工朱碧山所制作。槎杯以仙人乘槎游天河的的神話故事為題材,將酒杯巧制成樹槎形的一葉扁舟,槎上一老人背靠槎尾倚坐,長須髯髯,雙目注視遠方,一手撫膝,另一手撐于槎面,前部有一開口,以作盛酒之用。該銀槎杯出自乾隆年間刑部尚書、蘇州人韓崶墓中,1974年被吳縣文物工作人員征集。1994年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2020年蘇州吳中博物館成立并對外開放,由吳中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移交吳中博物館,進入博物館基本陳列中。


槎,通查,意為水中浮木,即漂浮水上帶枝杈枯木,因可載人而行,后被用作木筏的代稱。在我國古代,濱海地區水天相接的自然景觀容易讓人們誤認為天上的天河與陸地的大海是相通的,因此海邊的居民常有心尋找天河一事。因此,人們將這種奇異、神奇能夠往來于海上和天河之間的木筏飛行物,稱之為浮槎、仙槎、海槎、星槎等。目前主流認識仙人乘槎中的人物形象是漢代鑿空西域的張騫,但是究竟何時仙人乘槎和張騫窮河源故事合流形成張騫乘槎典故?目前學界并沒有定論。
仙人乘槎典故則最早見于西晉張華(公元232-300年)所著《博物志》一書: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查(槎)上,多赍糧,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余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記載的是海邊一居民乘槎泛海漂去,遇牛郎織女的奇遇的故事,舊說云說明該傳說在書中記載之前就已經產生,但故事并未與張騫或者窮河源產生聯系。張騫窮河源一事最早見于《史記》,書中對張騫通西域到達黃河源頭僅是一種客觀事實的描述,并未與乘槎遇牛郎織女相聯系,更談不上任何神跡色彩。
東晉王嘉(?-390年)所作的神話志怪小說集《拾遺記》中記載有貫月槎的典故: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 亦謂掛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群仙含露以漱, 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說明在東晉時期,這類通天的巨槎已經和具有濃厚神性的羽人相聯系,神話傳說色彩也愈加濃厚。
宋代的《太平御覽》中保存了南朝劉義慶《集林》中一則故事:昔有一人尋河源,見婦人浣沙,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說明劉義慶(公元403-444年)在著《集林》時故事的主角顯然還未明確,仙人乘槎和張騫窮河源還屬于兩個單獨的故事,但兩個故事的目的都已經明確為尋河源之事,為以后兩個故事的合流作出了鋪墊。
到南朝的庾肩吾(公元487-551年)和庾信(公元513-581年)父子時,本來沒有名字的居海者、一人等開始被冠以漢使稱謂,如庾肩吾《奉使江州舟中七夕詩》:天河來映水,織女欲攀舟。漢使俱為客,星槎共逐流。、庾信《七夕》:牽牛遙映水,織女正登車。星橋通漢使,機石逐仙槎。由漢使和尋河源很自然的讓人聯想到張騫受漢武帝命令尋找黃河源頭的事件。最終在南朝宗懔(502-565年)所著《荊楚歲時記》中就有了張騫尋河源,所得榰機石示東方朔的故事,書中將這一故事主角的形象具體化,正式明確為通西域的博望侯張騫。
清代劉廷璣在所撰的《在園雜志》中收錄了南朝的謝靈運(385-433年)所作的《青蓮》一詩,詩中我道玉衡邀,織女則不樂。昔日張騫槎,怪他悤悤過。提到了張騫槎一詞。如果《青蓮》一詩真的是謝靈運所作,應該是目前已知最早張騫槎的記錄。但劉廷璣在《在園雜志》中記載所錄的這些詩文是浙東單友以扶乩之技刻畫沙詩詞不下數百僅存的數十首,扶乩是古代的一種迷信的占卜方法,劉廷璣在書中將《青蓮》認為是謝靈運所作顯然不具有科學性,因此將仙人乘槎中的仙人形象認為是在謝靈運所處時代即公元385年到433年之間已轉變成張騫的說法并不具說服力。
由此,仙人乘槎故事的產生應不晚于張華所處的西晉,其中仙人形象附會為通西域的張騫的時間約是在南北朝時期,更具體的時間應是南朝劉宋朝到蕭梁朝的100余年間。這一時期政權更迭頻繁,社會動蕩,為產生于東漢末年的道教進一步傳播提供了土壤。道教通過描述仙界的存在證明得道成仙的可能,帶動泛海、游仙之類的故事風行。道教在傳播過程中將著名的歷史人物與得道成仙之說融合,可以讓這一類傳說更具有說服力,吸引信眾的相信。
隋唐時期是張騫乘槎之說的高潮期,其故事的傳奇性與神話浪漫主義色彩完美貼合唐代文學中獵奇的文風,使得這一時期無論是上層社會的賦詩作文,亦或是面向普通大眾的民間文學作品中張騫乘槎典故廣泛出現,當時的文人們通過張騫乘槎的故事,傳達一種翱然物外的灑脫與理想情懷。詩圣杜甫就有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有感五首》)、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詩》)之句。正是通過唐代文人的演繹,使得仙人乘槎中仙人形象與張騫進一步融合,并得以廣泛流傳。唐代后期,張騫乘槎之說的盛行也使得當時的文人開始對其故事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唐后期的李肇、趙璘在所撰寫的《唐國史補·因話錄》中就曾對張騫槎真偽表示質疑,認為前人詩文中使用張騫槎稱呼是因為相襲謬誤,且縱出雜書,亦不足據。
宋元以降,隨著文人繪畫藝術的興起,使得人物故事藝術題材的作品日漸增多,張騫乘槎典故也呈現出由文學作品到現實具象化的轉變,其圖案開始在工藝美術品上流行起來。
北宋時期,其形象開始以平面紋飾加以表現,如畫家李公麟就曾以張騫乘槎故事為原型繪制過《東坡乘槎圖》,可惜此畫未能流傳下來,僅在南宋周紫芝的《李伯時畫東坡乘槎圖贊》一書中有過記錄。目前發現最早的此類題材形象使用實例是2005年浙江溫州山前街建筑工地出土的北宋青釉浮雕乘槎執壺(圖三),壺的腹部前后各浮雕張騫乘槎圖,有意思的是該壺上兩幅圖案人物形象具有明顯不同,一面刻劃的是一位飽經風霜的老者形象,方臉,滿臉絡腮胡,雙目細長,炯炯有神;另一面卻是一壯年人物形象,但為圓臉,少須,側身但雙目正視,鎮定自若。但可以看出壺上張騫和浮槎的形象都較為抽象,略顯簡單,明顯處于圖像使用的初始階段。
圖三 北宋青釉浮雕乘槎執壺 溫州博物館藏
南宋時期,張騫乘槎形象開始變得細膩且愈加生動。江西九江瑞昌市博物館藏有一面1986年楊林湖基建工地出土的南宋仙人乘槎鏡(圖四),鏡紋內區飾一人物乘坐樹槎在波濤起伏的大海中行駛紋飾,外區飾象征黃道十二宮的十二座亭形小宮環繞,內有人物、動物等紋飾。2004年日本根津美術館曾舉辦一場名為宋元之美——以傳來漆器為中心的展覽,展覽中展出了一件直徑19.8厘米,由黑、赤、黃三色漆錯施漆層后剔出不同顏色圖像的南宋堆黑張騫銘漆盤(圖五),盤中心的右側正是一幅仙人乘槎的圖案,仙人形象生動傳神。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南宋時期的張騫乘槎形象相較于北宋青釉浮雕乘槎執壺上的圖案顯得更加生動且更成熟,與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元代朱碧山所制槎杯上的仙人乘槎形象頗為相似。
圖四 南宋仙人乘槎紋飾銅鏡 瑞昌市博物館藏
圖五 南宋堆黑張騫銘漆盤 日本私人藏
元代張騫乘槎故事進一步和世俗生活融合,不僅多次在出現在面向市井百姓的雜劇中,如馬致遠《江州司馬青衫淚》:他便以莽張騫天上浮槎,可原來不曾到黃泉下、鄭光祖《迷青瑣倩女離魂》:趕王生柳外蘭舟,似盼張騫天上浮槎、劉君錫《龐居士誤放來生債》:我不比那漢張騫,泛浮槎探九曜星臺、王伯成《李太白貶夜郎》:流落似守汨羅獨醒屈原,飄零似浮泛槎沒興張騫等。而且這一時期張騫泛槎形象更是以飽滿立體的槎形器物呈現,出現了朱碧山銀槎杯、張騫浮槎玉洗這樣技巧繁復、極富浪漫主義形式的工藝珍品。
圖六 元代張騫浮槎玉洗 舊金山亞洲藝術館藏
明清時期是仙人乘槎形象使用的蓬勃期,其形象被大量運用在書畫、瓷器、玉器、犀角器、竹木器等工藝美術品中,槎形器物更是大量出現,其中以槎形酒杯為主,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明晚期至清早期犀角雕仙人乘槎杯、清代尤通犀角槎杯、清代鏤雕花木老人犀角槎杯、明末犀角鏤雕花木人物槎杯,上海博物館收藏明代鮑天成所制的犀角雕浮槎杯,揚州博物館收藏明代仙人乘槎犀角杯(圖七)等。這些槎形酒杯,造型古雅,刻畫纖麗,十分珍貴,在貼合仙人乘槎傳說的同時,也借此傳達出一種與朋暢飲的歡愉之情。
圖七 存世明清時期槎形犀角杯
(1、2、3、4為故宮博物院收藏尤通犀角槎杯、犀角雕仙人乘槎杯、雕花木老人犀角槎杯、犀角鏤雕花木人物槎杯;5、上海博物館藏明代鮑天成制犀角雕浮槎杯;6、揚州博物館藏明代仙人乘槎犀角杯)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的還將祝壽寓意附加于仙人乘槎形象上,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中期的麻姑獻壽仙槎竹根雕,蘇州博物館收藏的清道光年粉彩諸仙乘槎祝壽紋碗,四川宜賓市博物院也收藏有一件清代粉彩開光人物瓷缸,缸上也繪有八仙乘槎賀壽的畫面。2017年西泠印社的秋季拍賣會上也曾拍賣一件長41厘米,寬27厘米的清中期粉彩八仙賀壽圖瓷板,圖案中間為五位仙人乘槎漂浮于仙海中畫面。(圖八)在中國民間傳說中,每年的農歷三月三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生辰,到了這一天群仙都會齊聚瑤池為其賀壽。這些祝壽寓意的乘槎圖案描述的正是這一民間傳說,借此傳達壽誕綿綿,長生不老的美好愿望。雖然這一類祝壽題材的乘槎形象已經和朱碧山銀槎杯表現的意義截然不同,但是顯然是經過仙人乘槎這一母題演化而來。
這一時期大量同類型題材工藝品的出現,說明仙人乘槎形象已經完全融入中國傳統吉祥意味紋飾圖案體系中。
圖八 清代祝壽寓意仙人乘槎圖案器物
(1、故宮博物院藏清中期麻姑獻壽仙槎竹根雕;2、蘇州博物館藏清道光粉彩諸仙乘槎祝壽紋碗;3、宜賓市博物院藏粉彩開光人物瓷缸;4、西泠印社秋拍清中期粉彩八仙賀壽圖瓷板)
參考文獻
1. 蘇州市吳中區博物館編:《吳中博物館圖錄》,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年。
2. 張志新:國寶征集的那些事兒——朱碧山造銀槎杯的征集,中國文物報,2016年2月2日。
3.(宋)陳彭年:《宋本廣韻》,中國書店,1982年。
4.(晉)張華著、鄭曉峰譯注:《博物志》卷十《雜說下》,中華書局.2021年。
5.(漢)司馬遷撰、韓兆琦評注:《史記·列傳》,岳麓書社,2019年。
7.(晉)王嘉撰,(梁)蕭綺錄.拾遺記.齊治平,校注.中華書局,1988年。
8.(宋)李昉等編纂:《太平御覽》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9.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2011年.
10.(南朝·梁)宗懔著(隋)杜公瞻注:《荊楚歲時記》,中華書局,2020年。
11.(清)劉廷璣撰、張守謙點校:《在園雜志》卷四,中華書局。
12.(唐)杜甫:《杜詩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3.(唐)李肇、趙璘撰:《唐國史補·因話錄》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4.(宋)周紫芝撰:《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1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15. 伍顯軍:宋代甌窯青瓷的新發現與研究,東方博物,第三十五輯。
16. 吳水存編著:《九江出土銅鏡》,文物出版社,1993年。
17.(日)根津美術館編:《宋元之美——以傳來的漆器為中心》,日本寫真印刷株式會社,2004年。
18. 殷志強著:《旅美華玉——美國藏中國玉器珍品》,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19. 沈從文:《分瓜瓟斝與點犀?——關于<紅樓夢>注釋一點商榷》載《花花朵朵、壇壇罐罐》,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
聲明:本館原創文章轉載,須經館方授權。公益原創文章插圖,圖片版權歸屬于收藏地或創作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責任編輯:
注明:本文章來源于互聯網,如侵權請聯系客服刪除!